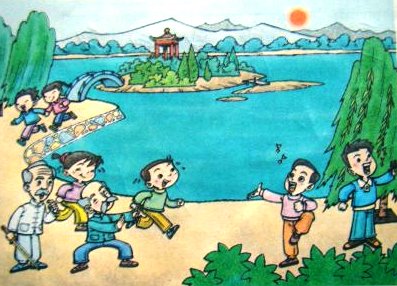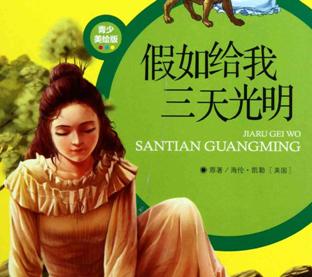源頭活水,生意長(zhǎng)流-作文專項(xiàng)訓(xùn)練教程
源頭活水,生意長(zhǎng)流-作文專項(xiàng)訓(xùn)練教程—從生活中取材
眾所周知,巧婦難為無(wú)米之炊。無(wú)論怎樣能干的媳婦,沒(méi)有“米”,也是做不出飯的。寫(xiě)文章同樣道理,沒(méi)有充分、生動(dòng)和質(zhì)地優(yōu)良的材料,只在技巧上兜圈子,翻花樣,寫(xiě)出來(lái)的文章必然是內(nèi)容干癟,面目可憎。
文章不應(yīng)當(dāng)是“做”出來(lái)的,而應(yīng)該像汩汩的清泉,從心坎里流出來(lái)。心坎里的清泉來(lái)自何方?來(lái)自五光十色的生活,來(lái)自從生活中汲取材料的本領(lǐng)。須懂得:生活中源頭活水流淌,筆下的文章就生意長(zhǎng)流。
文心絮語(yǔ)
“理論是灰色的,而生活之樹(shù)是常青的。”這是德國(guó)大文學(xué)家歌德的一句名言。確實(shí)如此,生活之樹(shù)常青,生活是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寫(xiě)作源泉。
任何體裁的文章,都是一定的社會(huì)生活的反映,寫(xiě)文章,也就是寫(xiě)生活,學(xué)寫(xiě)文章的人,要在生活這一關(guān)上認(rèn)真下功夫,關(guān)心,了解,發(fā)現(xiàn),尋覓,感受。大腦中采集的自然與社會(huì)的信息越多,寫(xiě)作的素材越豐富。
要身入生活,心人生活,才會(huì)了解周圍的人和事,景與物,才會(huì)有所發(fā)現(xiàn)。每個(gè)人都生活在“生活”之中,可從生活中獲得的認(rèn)識(shí)與感受卻大相徑庭。
有的人目光敏銳,善于觀察,不僅像攝像機(jī)一樣能把客觀的物像攝人自己的眼簾,印入自己的腦海,而且能在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事物中發(fā)現(xiàn)一般人所看不到的新鮮東西,生動(dòng)的,帶著生活露水的;而有的人身在見(jiàn),聽(tīng)而不聞,雖然也用眼睛,但浮光掠影,至多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。二者比較,關(guān)鍵在是不是“身入”、“心入”。“身入”而“心”不“入”,生活中大量有趣的、有意義的、有價(jià)值的材料,就會(huì)從眼皮底下溜走;至于“身”不“入 ”,不認(rèn)真生活,不認(rèn)真實(shí)踐,那就更談不上從生活中取材了。
怎樣才能身入、心入呢?要對(duì)接觸到的人和事有濃厚的觀察興趣,學(xué)會(huì)觀察的方法。觀察,不只是用眼睛,還要用耳朵,用鼻子,不僅用感覺(jué)器官,更重要的是用“心”,用“心”去看,去聽(tīng),去想,去感受。
魯迅先生《社戲》中月下行舟的幾段文字就是身入生活、心入生活,從生活汲取生動(dòng)材料的典范。文中是這樣描述的:
“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輕松了,身體也似乎舒展到說(shuō)不出的大。一出門,便望見(jiàn)月下的平橋內(nèi)泊著一只白篷的航船,大家跳下船,雙喜拔前篙,阿發(fā)拔后篙,年幼的都陪我坐地艙中,較大的聚在船尾。母親送出來(lái)吩咐‘要小心’的時(shí)候,我們已經(jīng)點(diǎn)開(kāi)船,在橋石上一磕,退后幾尺,即又上前出了橋。于是架起兩支櫓,一支兩人,一里一換,有說(shuō)笑的,有嚷的,夾著潺潺的船頭激水的聲音,在左右都是碧綠的豆麥田地的河流中,飛一般徑向趙莊前進(jìn)了。
“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(fā)散出來(lái)的清香,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(lái);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氣里。淡黑的起伏的連山,仿佛是踴躍的鐵的獸脊似的,都遠(yuǎn)遠(yuǎn)地向船尾跑去了,但我卻還以為船慢。他們換了四回手,漸望見(jiàn)依稀的趙莊,而且似乎聽(tīng)到歌吹了,還有幾點(diǎn)火,料想便是戲臺(tái),但或者也許是漁火。
“那聲音大概是橫笛,宛轉(zhuǎn),悠揚(yáng),使我的心也沉靜,然而又自失起來(lái),覺(jué)得要和他彌散在含著豆麥蘊(yùn)藻之香的夜氣里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