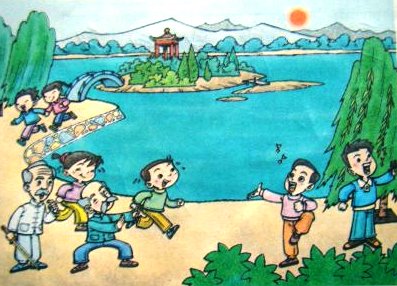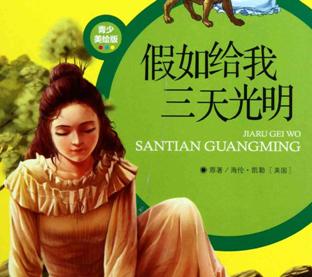用心靈走近蒲松齡-精品美文天天讀
用心靈走近蒲松齡-精品美文天天讀
一個(gè)人沿嶗山古徑攀援,直至嶗頂。在這與天穹比鄰的天界,擇石坐定。那蒼海波濤,翩飛鷗鳥(niǎo),盡收眼底;那陣陣經(jīng)聲,繚繞煙霧,也隨罡同一起遁入云端。一個(gè)人的世界,最易浮想。想到自己離開(kāi)生我的這片海邊熱土已近三十余載了,而這些年來(lái),我苦苦求索的精神之旅中,每每徘徊不定時(shí),冥冥中不時(shí)有一面容清癯的老者與我直面,讓我汗顏。我知道,他就是清代偉大的布衣作家蒲松齡。
我似一顆蒲公英的種子,從海邊起飛,降落在魯中的孝婦洞畔,一呆就是三十余年。一旦在這兒扎下•了根,就再也不想挪窩起飛了。在淄博,我經(jīng)常以地主的身份帶領(lǐng)外地客人去蒲家莊蒲松齡故居訪問(wèn)。歲月不居,前塵如海。蒲松齡既平凡近人又崇峻曠遠(yuǎn)的形象,便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靈深處。記不清去蒲家莊多少次,但給我印象刻骨銘心的還是我一人前往的第一次。
第一次去拜謁蒲松齡先生正是“文革”動(dòng)亂年代,當(dāng)我聽(tīng)說(shuō)蒲松齡的墓槨被挖開(kāi)了時(shí),我的心震顫了,便乘公共汽車(chē)到洪山,再沿鄉(xiāng)間泥路磕磕絆絆地去了蒲氏墓園。那時(shí)墓園沒(méi)有圍墻,老遠(yuǎn)就能見(jiàn)到幾叢高大的古柏下新挖的黃土堆積如丘。走近了,看清墓穴洞開(kāi)著,只見(jiàn)些許朽木、碎骨、發(fā)絲,墓地周遭紙灰飄零,據(jù)附近一老者言,這是墓中一部書(shū)的殘跡。這是一部從未面世的書(shū),是作者臨終前叮囑家人務(wù)必與其合葬的一部書(shū)。
果真如此,這太可悲了。日后若以現(xiàn)代高科技攝像技術(shù),必將全真跡大白于天下。先生《聊齋志異》成書(shū)后,王漁洋1688年題寫(xiě)了那首著名的《戲書(shū)蒲生<聊齋志異>卷后》的絕句:“姑妄言之姑聽(tīng)之,豆棚瓜架雨如絲。料應(yīng)厭作人間語(yǔ),愛(ài)聽(tīng)秋墳鬼唱時(shí)。”這一年,蒲松齡48歲,離他駕鶴西去,還有27年的人生旅程,作為一生勤奮筆耕的蒲留仙,決不會(huì)坐等時(shí)光,我想墳前這部“飛天”之作,很可能就是他繼《聊齋志異》之后,又一部力作。我想,在寫(xiě)作上,或許會(huì)丟掉他慣用的狐鬼花妖的表現(xiàn)形式,而選擇直抒胸臆的筆觸,既然要去另一世界閱讀,就不必再諱避文字獄的加害了。
上述王漁洋“戲書(shū)”的絕句,肯定了《聊齋志異》源于民間生活的現(xiàn)實(shí)意義和藝術(shù)價(jià)值,卻忽略了作者創(chuàng)作此書(shū)的“孤憤”襟懷。蒲松齡在《次韻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見(jiàn)贈(zèng)》言道:“《志異》書(shū)成共笑之,布袍蕭索鬢如絲。十年頗得黃州意,冷雨寒燈夜話時(shí)。”這就讓我們真真切切地看清楚寒夜燈下,一個(gè)受難的知識(shí)分子,面對(duì)自己靈魂的拷問(wèn)和鞭笞。這與《聊齋志異》所言:“集腋為裘,妄續(xù)幽冥之錄;浮白載筆,僅成孤憤之書(shū):寄托如此,亦足悲矣!”正說(shuō)明作者是有所寄托的,而并非僅為“姑妄言之”。
“文革”期間,蒲松齡故居的大門(mén)被一把銹鎖將其與外邊瘋狂的喧囂隔開(kāi)。當(dāng)我被留守故居的蒲玉水老人從一個(gè)便門(mén)帶進(jìn)院內(nèi)時(shí),頓覺(jué)寂靜異常,滿(mǎn)院荒草離離,墻壁、屋宇都露出些破敗的樣子。蒲松齡居住過(guò)的正房那紙糊著的窗欞,被風(fēng)當(dāng)作口哨不時(shí)吹響,幾只麻雀從窗欞間飛進(jìn)飛出,我們步入屋內(nèi),見(jiàn)幾樣破舊物件隨便地堆在地上,正面懸掛“聊齋”匾額的背后,已被一對(duì)麻雀夫婦選作生兒育女的暖巢,破敗至此,令人不免心寒。但當(dāng)我聽(tīng)到蒲玉水介紹說(shuō),蒲松齡墓穴中出土的印章、燈臺(tái)、酒盅等什物,還都保存完好時(shí),我不僅感到這個(gè)死后不得安寧的靈魂,日后必將還有重修墓園之日。我相信:泯滅的是肉體,而不死的是靈魂。
一個(gè)人沿嶗山古徑攀援,直至嶗頂。在這與天穹比鄰的天界,擇石坐定。那蒼海波濤,翩飛鷗鳥(niǎo),盡收眼底;那陣陣經(jīng)聲,繚繞煙霧,也隨罡同一起遁入云端。一個(gè)人的世界,最易浮想。想到自己離開(kāi)生我的這片海邊熱土已近三十余載了,而這些年來(lái),我苦苦求索的精神之旅中,每每徘徊不定時(shí),冥冥中不時(shí)有一面容清癯的老者與我直面,讓我汗顏。我知道,他就是清代偉大的布衣作家蒲松齡。
我似一顆蒲公英的種子,從海邊起飛,降落在魯中的孝婦洞畔,一呆就是三十余年。一旦在這兒扎下•了根,就再也不想挪窩起飛了。在淄博,我經(jīng)常以地主的身份帶領(lǐng)外地客人去蒲家莊蒲松齡故居訪問(wèn)。歲月不居,前塵如海。蒲松齡既平凡近人又崇峻曠遠(yuǎn)的形象,便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靈深處。記不清去蒲家莊多少次,但給我印象刻骨銘心的還是我一人前往的第一次。
第一次去拜謁蒲松齡先生正是“文革”動(dòng)亂年代,當(dāng)我聽(tīng)說(shuō)蒲松齡的墓槨被挖開(kāi)了時(shí),我的心震顫了,便乘公共汽車(chē)到洪山,再沿鄉(xiāng)間泥路磕磕絆絆地去了蒲氏墓園。那時(shí)墓園沒(méi)有圍墻,老遠(yuǎn)就能見(jiàn)到幾叢高大的古柏下新挖的黃土堆積如丘。走近了,看清墓穴洞開(kāi)著,只見(jiàn)些許朽木、碎骨、發(fā)絲,墓地周遭紙灰飄零,據(jù)附近一老者言,這是墓中一部書(shū)的殘跡。這是一部從未面世的書(shū),是作者臨終前叮囑家人務(wù)必與其合葬的一部書(shū)。
果真如此,這太可悲了。日后若以現(xiàn)代高科技攝像技術(shù),必將全真跡大白于天下。先生《聊齋志異》成書(shū)后,王漁洋1688年題寫(xiě)了那首著名的《戲書(shū)蒲生<聊齋志異>卷后》的絕句:“姑妄言之姑聽(tīng)之,豆棚瓜架雨如絲。料應(yīng)厭作人間語(yǔ),愛(ài)聽(tīng)秋墳鬼唱時(shí)。”這一年,蒲松齡48歲,離他駕鶴西去,還有27年的人生旅程,作為一生勤奮筆耕的蒲留仙,決不會(huì)坐等時(shí)光,我想墳前這部“飛天”之作,很可能就是他繼《聊齋志異》之后,又一部力作。我想,在寫(xiě)作上,或許會(huì)丟掉他慣用的狐鬼花妖的表現(xiàn)形式,而選擇直抒胸臆的筆觸,既然要去另一世界閱讀,就不必再諱避文字獄的加害了。
上述王漁洋“戲書(shū)”的絕句,肯定了《聊齋志異》源于民間生活的現(xiàn)實(shí)意義和藝術(shù)價(jià)值,卻忽略了作者創(chuàng)作此書(shū)的“孤憤”襟懷。蒲松齡在《次韻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見(jiàn)贈(zèng)》言道:“《志異》書(shū)成共笑之,布袍蕭索鬢如絲。十年頗得黃州意,冷雨寒燈夜話時(shí)。”這就讓我們真真切切地看清楚寒夜燈下,一個(gè)受難的知識(shí)分子,面對(duì)自己靈魂的拷問(wèn)和鞭笞。這與《聊齋志異》所言:“集腋為裘,妄續(xù)幽冥之錄;浮白載筆,僅成孤憤之書(shū):寄托如此,亦足悲矣!”正說(shuō)明作者是有所寄托的,而并非僅為“姑妄言之”。
“文革”期間,蒲松齡故居的大門(mén)被一把銹鎖將其與外邊瘋狂的喧囂隔開(kāi)。當(dāng)我被留守故居的蒲玉水老人從一個(gè)便門(mén)帶進(jìn)院內(nèi)時(shí),頓覺(jué)寂靜異常,滿(mǎn)院荒草離離,墻壁、屋宇都露出些破敗的樣子。蒲松齡居住過(guò)的正房那紙糊著的窗欞,被風(fēng)當(dāng)作口哨不時(shí)吹響,幾只麻雀從窗欞間飛進(jìn)飛出,我們步入屋內(nèi),見(jiàn)幾樣破舊物件隨便地堆在地上,正面懸掛“聊齋”匾額的背后,已被一對(duì)麻雀夫婦選作生兒育女的暖巢,破敗至此,令人不免心寒。但當(dāng)我聽(tīng)到蒲玉水介紹說(shuō),蒲松齡墓穴中出土的印章、燈臺(tái)、酒盅等什物,還都保存完好時(shí),我不僅感到這個(gè)死后不得安寧的靈魂,日后必將還有重修墓園之日。我相信:泯滅的是肉體,而不死的是靈魂。
本文標(biāo)題:用心靈走近蒲松齡-精品美文天天讀
電腦版地址:http://www.jqlj.com.cn/sucai/meiwen/5751.html
手機(jī)版地址:http://m.fanwen.co/sucai/meiwen/5751.html
電腦版地址:http://www.jqlj.com.cn/sucai/meiwen/5751.html
手機(jī)版地址:http://m.fanwen.co/sucai/meiwen/575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