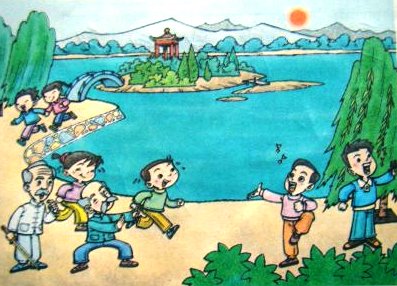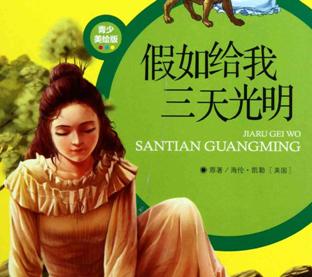和你一起學作文-小說的基礎知識
和你一起學作文-小說的基礎知識
小說是一種敘事性的文學體裁,它通過刻畫鮮明的人物形象,敘述完整的故事情節,描寫具體的背景環境,廣泛而細致地反映社會生活。
我國小說的歷史是悠久的。一般認為,小說始于古代神話和傳說,漢魏六朝有一定發展,但無論從人物塑造或情節描寫來看,都顯得不成熟,比較粗簡;同時,小說的概念也很混亂,往往成為傳聞異錄或歷史佚事的總稱。到了唐代,中國小說漸漸發育成形,具有了比較完備的藝術形式和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內容。魯迅說:“小說亦如詩,至唐代而一變,雖尚不離搜奇記逸,然敘述宛轉,文辭華艷,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,演進之跡甚明,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。”
在唐代,人們稱小說為傳奇。其著名作品有《古鏡記》、《游仙窟》、《枕中記》、《南柯太守傳》、《柳毅傳》、《李娃傳》、《霍小玉傳》、《鶯鶯傳》、《虬髯客傳》等。
“話本”在宋代的出現,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。這種白話小說更廣泛地反映了社會生活,特別是中小商人、手工業者和下層婦女的生活。在語言上運用了接近口語的白話,在藝術上,如描寫人物、環境和對話方面也有新的發展。可惜的是,宋代話本流傳下來的只有二三十篇。其中突出的有《碾玉觀音》、《鬧樊樓多情周勝仙》和《快嘴李翠蓮》等。宋代話本除小說外,還有講史,如《大宋宣和遺事》,此書與《水滸傳》的形成有重大關系。
經過宋元兩代的長期孕育,中國的小說到了明代,取得了極高的成就。著名作品有羅貫中的《三國演義》、施耐庵的《水滸傳》、吳承恩的《西游記》等。以上均為長篇小說。短篇小說則有馮夢龍的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和《醒世恒言》,凌濛初的《拍案驚奇初刻》和《拍案驚奇二刻》,而《今古奇觀》則為“三言二拍”的選本。
清代小說繼續發展。蒲松齡的《聊齋志異》是文言短篇小說的最高成就;吳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是古代諷刺文學最優秀的作品;而曹雪芹的《紅樓夢》在文學史上的價值,則不僅是中國的,而且是世界的。魯迅說:“至于說到《紅樓夢》的價值,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不可多得的。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,并無諱飾,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,壞人完全是壞的,大不相同。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,都是真的人物。總之自有《紅樓夢》出來以后,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。——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,倒還是在其次的事。”清末小說的創作也很繁榮,其重要作品有李寶嘉的《官場現形記》、吳研人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和劉鶚的《老殘游記》。
“五四”運動后,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小說出現,至今已獲得很大的發展。
小說的特征可以概括為:人物形象的鮮明性,故事情節的完整性,和環境描寫的具體性。小說的創作不受真人真事的局限,允許而且必須在深入生活的基礎上,進行藝術的概括、虛構和升華。
人物,是小說的主要描寫對象。整篇小說的內容都是圍繞人物性格的形成和發展來安排的。所以,典型人物的塑造,就在小說創作中占據了中心的地位。當然,高爾基曾說:“文學就是人學”,所以廣義地講,任何文學作品都是為了寫人。但和其它文學形式相比,小說的容量最大。它反映社會生活不像戲劇那樣,要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。在語言運用上,它不像抒情詩那樣,只有抒情主人公的語言;也不像戲劇那樣,只有角色的語言。小說不僅有敘述人的語言,而且有人物的語言,兩者交替運用,有很大的靈活性。小說的人物形象,不受真人真事的限制,可以而且必須在符合生活真實的基礎上進行虛構,結果就產生了一種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典型化了的人物形象,它具有更強的藝術感染力。魯迅在談到塑造典型人物時說:“往往嘴在浙江,臉在北京,衣服在山西,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。”小說中的典型人物,既要有共性,又要有個性。沒有共性,人物就失去了代表性,不成其為典型;沒有個性,人物就不可能鮮明生動,也不可能成為典型。
情節是構成小說的重要因素,是作品的大綱和骨架。它是由生活矛盾所構成的事件,是人物之間的關系。離開了一定的,相對完整的故事情節,就無法表現人物的性格,也就不能表現小說的主題思想。看過《三國演義》的人都知道,如果沒有“舌戰群儒”、“草船借箭”、“借東風”、“空城計”等一系列情節,諸葛亮的人物性格是不可想象的。故事情節通常由開端、發展、高潮、結局等幾個部分組成。有時前面還有序幕,后面還有尾聲。小說情節的安排不一定按照事件發展的自然順序來展開,也有倒置的情況,也有輕重省略的考慮,具體運用起來是有很多變化的。
小說的敘述方式,最常見的是第一人稱、第三人稱,順敘、倒敘、插敘之類。所謂第一人稱,即假托“我”的所見所聞所思來寫。這樣寫的好處,是使讀者感覺比較真實,缺點是對敘述描寫有所限制,即不是“我”直接見聞的事情就不能寫。這種從“自知”角度寫小說的方法顯然對作者有較大的約束,于是又有一種更加自由的敘述方法,那就是第三人稱的寫法,即多角度的“全知全能”。采用這種寫法,作者就有了極大的自由,他對小說中所有的人和事,甚至各人的心理活動,都無所不知,無所不曉,于是就對自己的小說取得了無所不能的主宰權。這當然為小說家發揮創作才能開辟了更加廣闊的天地。由此可知,古今中外的小說大多使用第三人稱就不奇怪了。
最初,許多作者的觀察、體驗、敘述、描寫也完全是從自身的角度,用自己的眼光來寫。這就仿佛有一架攝像機,始終由作者帶著在工作,而講述、配音等工作也完全由作者來擔任。這樣寫,往往概括的敘述多,具體生動的描寫少,表現手法也顯得比較單調。這樣的小說當然就不怎么好看。很快,作家們就變得聰明起來了,他們讓小說的人物來配合自己的工作。比如林黛玉初見賈寶玉,“攝像機”就在她那兒,對賈寶玉的描寫,就由她來觀察體驗,從她的角度來表現;然后再通過賈寶玉來寫林黛玉,“攝象機”又到了賈寶玉那兒。再比如說作者寫賈府那樣的深宅大院,他沒有自己扛著“攝像機”去一一介紹,而是讓林黛玉進賈府的時候帶著一個“微型攝像機”,從她的角度看去,一面走一面介紹。這樣寫不僅方便,而且把敘述與人物和情節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了。